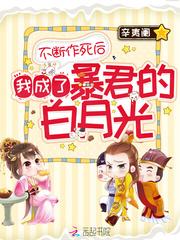69中文网>许君长乐 > 局中人(第2页)
局中人(第2页)
他似是也没想到,陛下会这样将立储这么大的事,当着他们两个少年人的面,就这么直接了当地说了个定。
他面朝地上,头几乎就要垂到地面,头顶的圣意还在宣布着——
“再封张淮之为太子太傅,你,协助老三修典有功,就随父一起,封为太子少傅,你张氏一族,往后便可永享帝师之荣。”接着,景和帝又稍带上一句,“江崇,随侍七皇子有功,待太子册立后,升为太子少保。”
他面上的态度再宽和不过了,送官送名,像是给张府找稳了退路,可内里,却是藏着盘算的——
张氏乃士族之首,让他为三皇子之师,一是为了借张氏之名,让下面的老臣认这个太子,二是让三皇子能借此笼络士族,未来也好防止外戚独大。
这样一来,两边制衡,才好让各方都能使唤得动。
眼见景和帝的一番话,直接将七皇子身边之人抽了个干净,张岁安跪在堂下,迟迟不敢开口答话。
侍立在旁的中常侍常玉见了,也刻意清咳了两声,提醒着张岁安回话。
“太子乃国之储君,臣……”张岁安叩着地面,竭力维持着语气的平稳,“臣资历浅薄,实在难以担此重任。”
景和帝也料到他会说些拒词,旋即不急不缓地悠悠说道:“昔日朕听闻,明堂辩议上,曾有一少年才子,言辞犀利,一语中的,论及帝号之称时,说——”他顿了顿,似是想不太起来了,转头瞥了眼身旁的常玉,问道,“说的什么来着?”
常玉微微躬身,将张岁安之前在明堂上的言论原封不动地答了出来:“回陛下,此人说,袭国的帝号不可除,帝王之尊永存于世,而政事之谋断,邦交之进退,自有臣子,鞠躬尽瘁。”
张岁安一怔,僵在堂下,认命似地闭上了眼。
那日在明堂发问之人,果然是宫中的人。或许从那时起,自己的一言一行,便早早地被记入了景和帝眼中。
景和帝望向张岁安,又搬出之前说服张淮之的那一套,拿着情怀,说着软话叹道:“若袭国臣子皆有此志,朕何愁大业难成啊?”
在景和帝看来,三皇子虽算不上明君,却胜在敦厚,赵氏一族虽算不上能臣,却胜在好使。
臣不在贤,而在可控。没有根基的臣子,才能依附于君王之下。
若真任由年幼的嫡皇子继承大位,那才真的是士族堆上长了个小小的皇帝,届时皇权旁落,东袭皇室又将形同虚设。
除非,有一种可能,便是东袭皇室祖坟冒青烟,得了个千古忠臣,此人既要有诸葛之智,还要有诸葛之忠,死心塌地,绝无二心。
可是这种理想之士难得,他做了这么多年皇帝,见惯了为权为利之人,早就不信这种冒着忠义之名,实则争权夺势的鬼话。
而张岁安,他有智,有谋,有家族,有身份,最难得的,是他还有着半分少年的心气。
他就是那个最适合为袭国献祭的臣子。
殿内气氛沉滞,唯有殿外几声颓懒的蝉鸣,闷闷作响。
最后,景和帝终于想起了夹在这盘棋中的小小幼子,他轻描淡写地说了句:“七皇子虽还年幼,但也并非不能破例,朕会给他个偏远的藩地,让他在外安稳一生,从此不再入绥京。”
话虽如此,却连景和帝自己也知道,他活着时,尚且能保证七皇子所谓的安稳一生,可来日三皇子即位,新帝登基,一纸诏令下达封地,七皇子难道还能抗旨不入朝觐见吗?
这孩子的出生,本就是个意外,从他生下来那天起,恐怕除了皇后,就没人真心盼望他活着。
作为一国之君,当以朝政为先,作为父亲,能保他半生,已是仁至义尽。
今日,景和帝提前在小辈面前露了底,也是为了让他们回去后,跟家中父辈通好气,别再争辩什么立嫡立庶了,各自安分守己地迎立储君吧。
张岁安跪了不过半柱香的时间,却仿若隔了一世。